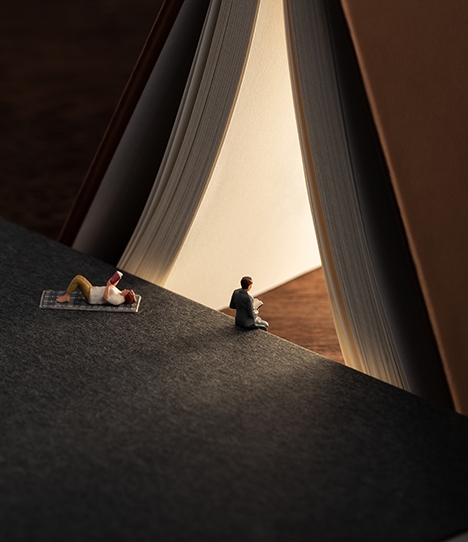人的一生,有些故事就像山里的萤火虫,明明灭灭,却始终闪着微光。这个清明时节,我们在追思先人之余,不妨读一读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书《青山隐》中那些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用猎枪守护家园,用双手创造生活,像路边的野草般顽强地活着。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生命最动人的光芒,其实就藏在这些认真活过的痕迹里,它们终将成为照亮人间路的点点星火,温暖前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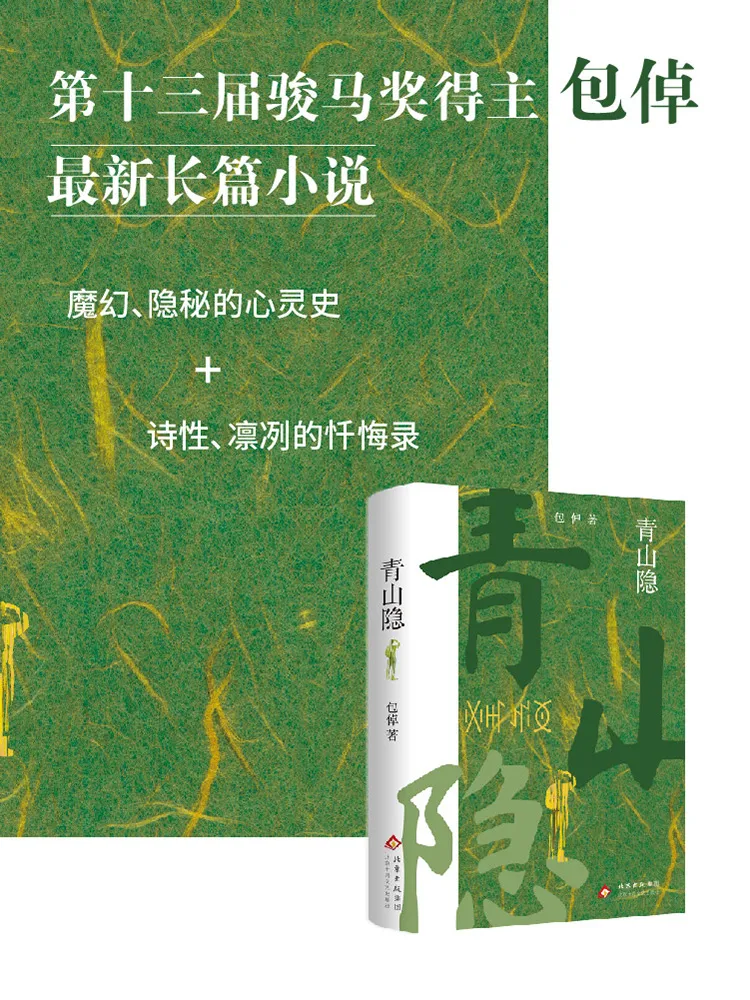
好书抢先看
猎人
文/包倬
活着是一种使命,也是一项义务。既然误打误撞来到这人间,又舍不得主动结束生命,那就只能艰难而热烈地活着。“干活”这个词,准确地道出了活着的真相——干,才有活路。这世界有五花八门的生活技能,种地应该算是技术含量较低的一种。不然,万千中国农民也不会见人就自觉矮三分。
比下地干活稍好一点的,是有一技傍身。这一点在瓦布尤为明显。古老的民间技艺,像路边的野草般顽强地活着。一代人来,一代人走,技艺永存。所以,从我记事时起,在初冬,总能遇见几个背着工具外出的瓦布人。
但邱百中是例外。作为世代猎人,他的舞台是瓦布周边的茂密山林。他除了种庄稼,就是上山打猎。他的猎枪,只在春天沉默。他之所以不时送猎物来与我们分享,其实是想找个人说话。他说什么?祖先的故事。这故事并不枯燥,但世间的故事,都经不起反复说。所以,瓦布老人有诫:话说多了是水。可邱百中不管这些。他总是说啊说,说的都是那些事。
“那时候。”他清了清嗓子,以此作为提示。
“那时候还没有瓦布,”我抢过话,并且学得有模有样,“那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原始森林,树大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
被抢了话,他也不在意,嘿嘿笑着,夸我记性好。其实我说得不对。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瓦布,而是那时候这片土地还没有被命名。
邱百中总告诉别人,第一个走到这里的人是他的祖先。关于他祖先怎样来到此地的有两个版本:一是打猎迷路,受萤火虫的指引而来;另有一说是被一头报恩的鹿驮着而来。他对瓦布其他姓氏的人这样说时,总遭到别人的质疑,因为他们都希望自己那些早已化成白骨的祖先是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只有我父亲,这个被发配到此地的乡村教师,从不和邱百中抬杠,并且还会火上浇油般送上几句夸赞。
“想想吧,”邱百中喝了酒,兴奋起来,站在屋子中央比画,“三间房子那么大的一团萤火虫,至少有上万只吧,它们抱成一团,点亮屁股上的灯,照着我家祖先走路。走了整整七个夜晚,才来到瓦布。”
“为啥只在夜晚走呢?”父亲适时提出疑问。
“害怕遇见猛兽嘛。”邱百中说。
“猎人还怕野兽?”
“那是猎枪,又不是机关枪。”邱百中强调,“一杆猎枪,只能对付一头野兽。而那时候,山里的野兽成群结队。”
“可惜了,”我父亲说,“生不逢时哪,不然,凭你家祖上的枪法,也能混个营长当当。”
邱百中一高兴,喝干了碗里的酒。这个生活在祖先崇拜中的人,一直靠神话活着。我见过他和其他姓氏的人争论谁的祖先最先来到瓦布,争到最后差点打起来。
“尹老师,真不是吹牛,如果没有我的祖先,就没有瓦布。”
“那是当然咯。这山里的飞禽走兽都是你邱家的,家里烧着水,上山去取便是。”
“还是有文化好。村里那些粗人,根本不懂历史。”
“你再给我们讲讲野兽的报复呗。”
“还想听?”他简直是大喜过望了,“那你们可要听好了。”
他的讲述带我们回到了遥远蛮荒的过去。说的是萤火虫引路的很多年以后,这地方已经被命名为瓦布。人和野兽的争斗从未间断。今天,人杀一只野兽;明天,野兽叼走一个孩子。那年秋天,野猪猖獗,瓦布的青壮年在邱家猎户的带领下进行了三次围剿。却没想到十天后,野兽大军成群结队而来,包围了瓦布,它们张着嘴,露出獠牙,杀气腾腾。不光有野猪,还有狼、豹子和豪猪。往常是猎人进山寻野兽,现在野兽主动找上门来了。从三岁小儿至耄耋老人,谁见过这阵仗?狼嚎,豹子叫,野猪呐喊,豪猪身上射出利箭,寒光闪闪。猎人们相约应战,但每个人端枪的手都抖得厉害。他们心里明白,那是猎枪。一旦枪响,要么野兽倒地,要么惹怒野兽,把人变成猎物。结果谁也不敢开枪,倒退而回。野兽把瓦布围了整整七天。第八天,有人率先放出了猪和羊,可那些猪羊只够野兽们塞牙缝。第十天。全村人都交出了猪和羊,甚至是牛和马,野兽们慢条斯理吃了个精光。野兽大军既不撤退,也不进攻。第十一天,有人走进了邱家的门。不是一两个,而是除邱氏以外的所有家族。他们肩挎猎枪或弓弩,甚至带来了酒和肉。他们绕山绕水地讲出了一个意思:平日里邱家猎户枪杀的野兽最多,结怨最大,这野兽的围攻得由邱家来化解。怎么化解?从天亮说到天黑,从天黑说到天亮,说尽了人间的好话歹话丑话狠话。
“我们邱家最好的猎人就这样举着双手一步步走向了野兽,野兽齐声嚎叫,村里人放声大哭。”
“人心真是太坏了。”
“尹老师,你说我祖上算不算英雄?”
“算,当然算,盖世英雄啊。”我父亲竖起大拇指,话锋一转,“对了,小春今天怎么没来?”
小春是邱百中的老婆,我叫她春孃孃。这个女人我见过几次,身上有雪花膏的味道。那味道和我母亲身上的味道一样。春孃孃跟着邱百中来我家,每次都会从衣兜里掏出糖来。她话不多,见谁都笑眯眯的。她坐在我家火塘边,拘谨得一根针落地都能吓一跳。有时候,她会轻声跟我说话,问:叫啥名字?几岁了?平时玩些啥?喜欢妹妹不?她讲话的口音跟我们不一样,需要努力分辨才能听清。
当我父亲提起春孃孃,母亲的目光如一道闪电凌空劈下。父亲突然噤了声。邱百中也像是被闪电劈了脑袋,好半天才回过神来。他说,小春是属兔的,不吃兔子肉。
“幸亏她不是属猪的。”母亲笑着,伸出筷子,夹起一块兔肉放进嘴里大嚼起来。
屋外,风吹过树林掀起声浪,继而如丝如缕,从门缝里钻进来,在屋里卷成团,从火塘边滚过,火苗呼地蹿起来。
“呸呸呸,”母亲吐着唾沫,顺便把嘴里的骨头也吐了出来,“这骚风,半夜三更也不停歇。”
父亲和邱百中继续喝酒,他们谈兴正浓,讲完了邱家先人的故事,又讲起瓦布的其他人。他们提起一些人名,但我并不熟悉。我的世界小得可怜,认识的人屈指可数。也许正是这样,我对我认识的人、他们的言行以及我的心境,都有着摄像机一般的记忆。
我喜欢白天。白天,这个世界是活的。瓦布小学书声琅琅,麻雀在窗外的枝头上一唱一和。我虽然还没到上学年龄,可我喜欢听他们读书。而夜晚呢,空气黏稠、冰冷,呈块状,难以下咽。父亲的书桌上放着一台砖头大小的收音机,但它要在父母心情好时才能出声。那时我以为,收音机里住着无数会说话和唱歌的小人,而电池则是请他们开口的钥匙。可某天我捡到一节废电池,敲开,里面是黑色的炭条、炭粉和白线。大失所望——我还以为电池里面也有小人儿呢。某天趁父母上课之机,我拿过收音机摸索,摸着摸着它突然唱起歌来。我吓了一跳。担心父母回来挨骂,却始终找不到开关。巧慧被音乐吵醒了,边哭边踢腿。慌乱之中,收音机从我手里掉落地上。这下好了,它终于不出声了,一片长条状的塑料盖子飞开,一节电池逃了出来。我跟着巧慧一起大哭,直到母亲下课回家。收音机摔坏了,父亲给了我屁股两巴掌。然后,他从抽屉里找出起子,准备自己动手修。他拆开外壳,露出里面五颜六色的零件。我泪渍未干,凑到父亲身边,发现那些零件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能歌善舞的小人儿。他用起子这里戳戳,那里拧拧,但收音机始终没响动。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他突然一声怒吼,将收音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如此,他还不满意,又找出斧头,把收音机砸了个稀烂。然后,他对我说,这些零件,你捡去玩吧。
可怕的不是爆发,而是沉默,像我父母在家里时那样。仿佛家里那道门具有某种魔力,能让他们在进出之间判若两人。我过早学会了察言观色,正是因为父母阴晴不定的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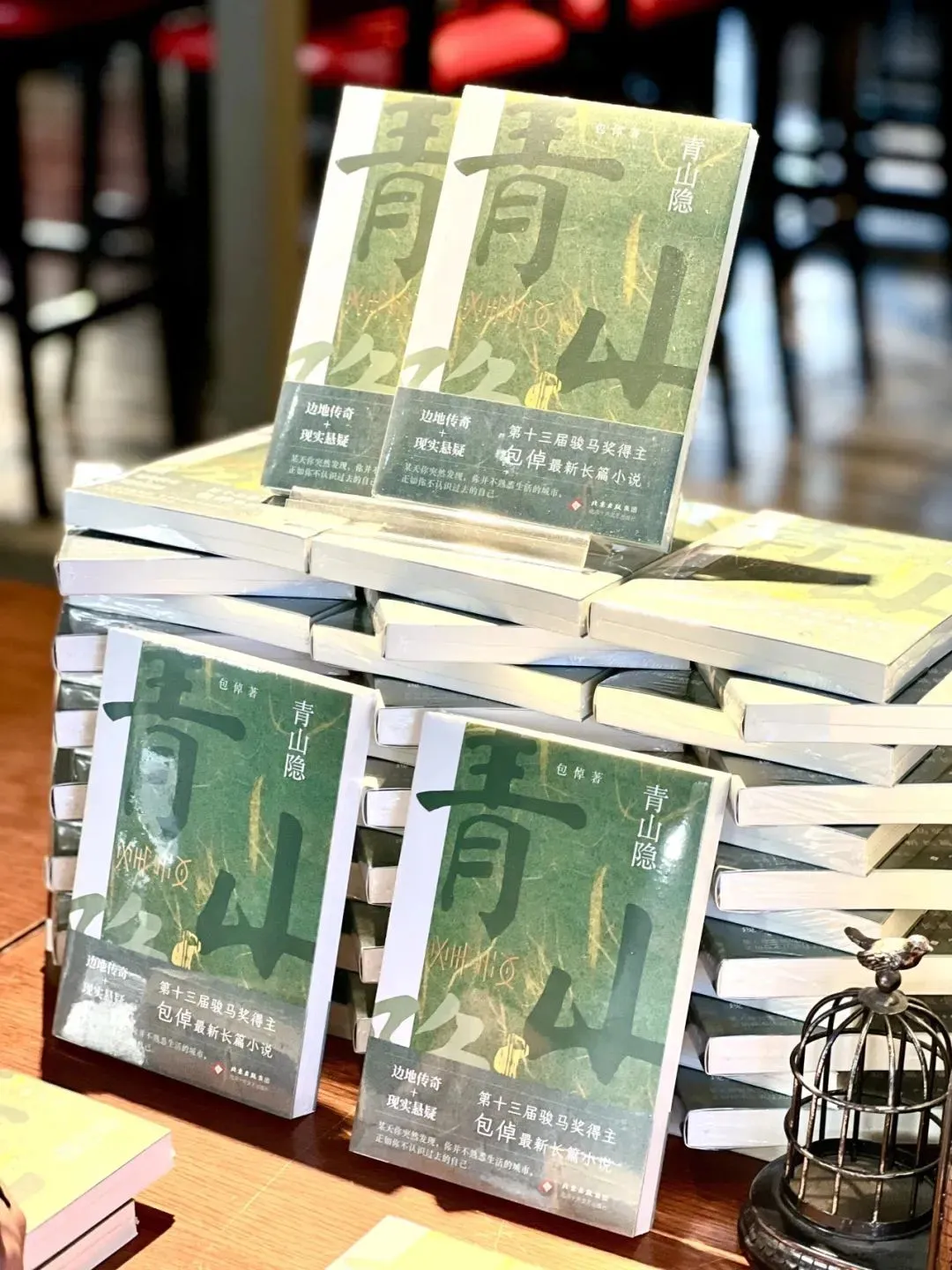
在外面,他们是让人尊重的教师。穿着干净整洁,讲话彬彬有礼。即使生活在乡村,他们也走在时代的前沿。父亲每两个月去一趟县城,走山路,搭客车,回来时总会给我们添一两件新衣服。收音机被砸烂了,他去县城买回一台录音机和十盒磁带。此后,课间休息时,他将音量调到最大,窗外挤满了学生的小脑袋。他某次进城,骑回来一辆自行车,学生们围着自行车看了很久。而母亲呢,如果不发怒,她算得上个美人,衣柜里挂满衣服,从人群中走过时香香的,总能引人注目。
我那时的愿望是巧慧能快一点长大,至少不要像根绳子似的绊住我。父母去上课,我的任务就是看守巧慧。可她尚在襁褓中,根本无法交流。我把她当成一团面,擀啊擀,然后我们一起睡着了。所以,在那些日子,一旦父母下课,我便离巧慧远远的。早上,我拿着小马扎坐在学校门口的梨树下,看着一个个学生奔跑而来。晚上,在同样的位置,我目送他们疲惫远去。那棵梨树花开花谢三次,我已经长到六岁。妹妹会走路了,她像尾巴似的整天跟着母亲。我去过每一间教室,每一个角落,包括女厕所。我在女厕所的蹲坑上尿不出来。世界真小,还四处禁区。山上不能去——如果被山魈抓走,会被它训练成野人。水边不能去——有人听见过娃娃鱼的哭声。如此,能去的地方也只有学校、乡政府和卫生院。可我不喜欢去乡政府的院子里玩,那些干部要么绷着脸,要么拿我寻开心。卫生院里那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也令人害怕,某次那个男医生居然举着针筒问我,打针不?那个女医生有点胖,满脸雀斑,喜欢涂口红。她经常坐在医院门口织一件红色毛衣。有天我问她,你家是不是有很多红毛衣?她说,我织的是同一件毛衣。见我不明白,她又说,织了拆,拆了织,懂了吧?
我点了点头。但并不懂她说的意思。
以上是《青山隐》节选。
作者简介

包倬,1980年生于四川凉山,彝族。2002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小说和散文见《人民文学》《十月》《钟山》等刊。出版有小说集《沉默》《十寻》《路边的西西弗斯》等。曾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欧阳山文学奖、云南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中篇小说主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现居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