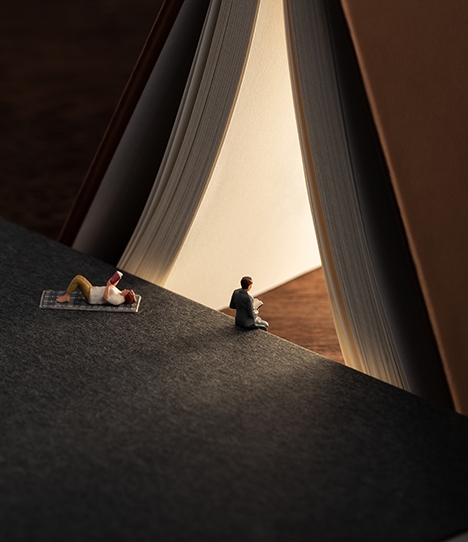李西岳
国家一级作家,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著有《百草山》《农民父亲》等,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撰写解说词。
向着天堂倾诉
文 / 李西岳
一晃,父亲走了整整五个年头了,这五年里,因为疫情和身体的原因,我没有做到每个清明节,或者父亲的忌日,都回老家上坟,也曾感到愧疚和不安,但转念又想,作为一名作家,纵使你在父亲坟前烧一大摞纸钱,磕一大堆响头,不如为他写本书,于是,就有了这本20万字的长篇散文《父子书》。有人说,忘记父母的日子,孝子贤孙不知道从哪一天算起,对于我来讲,就从这本书起算吧,为自己做一个了断,此后再也不受情感的折磨和寿命的折损了。经过几番思想斗争和多日冥思苦想,我开了这样一个头:“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能被写成一本书,但我的农民父亲可以。成为一本书的父亲,不一定高大伟岸、风流倜傥,不一定叱咤风云、功名千秋,但必须有坎坷的人生际遇、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不同寻常的人性温度。这些,我的父亲都具备。”开了这个头,我就可以畅快淋漓地与父亲对话,向着天堂倾诉了。
我知道,我的倾诉需要十足的勇气。平时与作家交流,大家都不愿写自己的家长里短,不愿触及自己的家事,不愿伤及自己的内心。卡夫卡说:“人们应该只读那些撕咬人的灵魂的东西。”要想撕咬读者的灵魂,首先就要撕咬自己,而我既然下了决心,就有勇气承受这种撕咬,就不怕触动内心的柔软,哪怕是从文字中溅出血泪。在我们家,曾遭遇许多撕咬人灵魂的事:待字闺中的姐突然精神抑郁;父亲58岁那年遭车祸髋骨摔伤;母亲一生病病殃殃;小弟32岁英年早逝……记得姐出院后,我利用探家归队的机会到天津谢恩,当三舅问我:“你爹好了吗?你娘好了吗?你姐好了吗?”我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好像自己家一个健康的人也没有,同时也暗自下决心,一定要长出息改变这个家的现状。如果说撕咬人灵魂的事,莫过于小弟遭车祸去世,我作为长兄为他穿寿衣,为他写挽联,站在丧者家属的最前面为他送行,抱着他的骨灰迈着蹒跚的脚步进入陵园,之后,我又“怕人寻问,咽泪装欢”,心照不宣而又诚惶诚恐地隐瞒父亲18年,这种灵魂撕咬太刻骨铭心了。我把这些都写出来了,要好的朋友说,真不知道你心里藏着这么大的秘密,还说,真没看出你瘦弱的身子骨儿还挺能扛事儿。家境的不幸是作家的幸运,而用文字呈现这些不幸,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做支撑,我的做法就像一把斧头一下凿开人们冰冻的心海,带给人们的是永无止境的精神折磨。作家往往是最敏感而脆弱的。我是眼窝很浅的人,遇到激动和悲伤的事,往往第一个掉泪失态的就是我。在尘世间,这些肯定不是什么优点,会成为一种困扰,写作的好处,在于通过写作可以获得自我拯救和治疗,可以把撕咬人灵魂的经历转变成写作的资源和财富。有人说,你这么像捅肺窝子地表达,书出来敢看吗?我倒觉得写出来之后,如释重负,心里轻松了许多。
我是写小说的,长篇、短篇都写了不少,虚构故事的能力还是有的,但散文属于非虚构,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把真实放在第一位,为什么作家们不愿写真实的自己,一是怕家丑外扬,再就是怕家人对号入座,惹出麻烦,往往善于把自己家里的事隐蔽在虚构文学作品里,或给当事人改个名字,或以真事为原型加一些虚构的东西,弄成似是而非的效果,但在《父子书》中,我把作家的那些小技巧都抛弃了,书中所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时间、事件完完全全都是真实的,都能跟活生生的人对上号,但我传达的是正能量,不会惹人家生气。
比如,父亲曾交给我一张纸条,上面记着好多人的名字,那些名字不光有大号,还有绰号,生怕不知道是谁,他在摔伤住院期间得到过这些人的帮助。那年,我往家捎了200斤大米,在那个年代,大米在老家是稀罕物,父亲按照名单挨家分送,最后家里所剩无几,他还要求我把有恩于己的人一一记在本上,一旦有机会就付诸回报,即使不能回报,也要在心里记一辈子。我真的按他老人家的要求做了。
还有一种真实,是来自情感的真实,作为作家,你只有把生命里最真实的情感倾注于笔端,作品才能呈现出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读者才会带着真情实感进入你的作品。《父子书》中,我当兵前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回这个家了是真实的,而在父亲灵前长跪不起也是真实的。父亲撵我提前归队是真实的,而每次站在村口拄着拐杖迎候我也是真实的。实际上,我在叙述中还渗透着强烈反思和心灵忏悔意识,告诉读者,自己在父亲身上留下诸多亏欠。我如此把自己的心亲手撕开让别人看,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可恰也给了我向着天堂倾诉的底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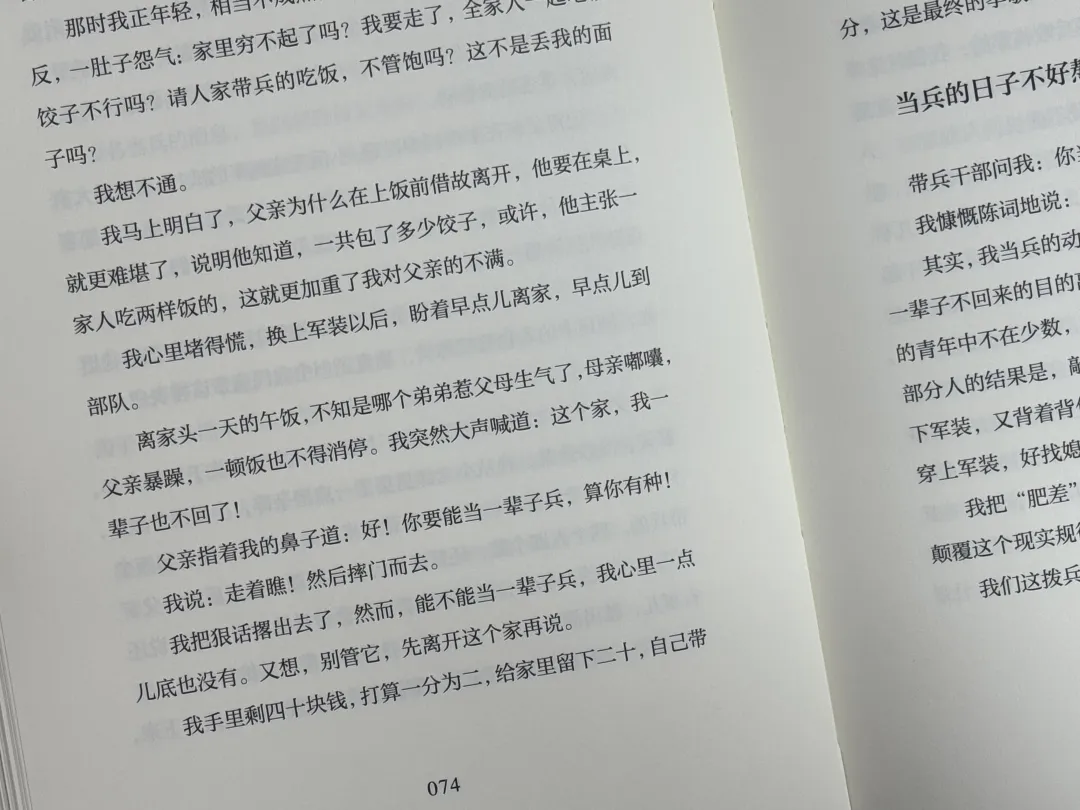
我还知道,我倾诉的声音应有艺术特色。我是写小说的,塑造典型形象是我的责任。《父子书》虽然是长篇纪实散文,但不能见事不见人,既然写人就得写出其典型意义,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我的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但他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年轻的时候走津门、闯关东,后来被奶奶揪回家,当过水利工程管理员、公社粮站保管员,3年自然灾害时期回村担任生产队队长兼会计,在县里举办的会计珠算比赛中拿过名次……也就是说,父亲在农民序列里还是相当了不起的存在。他的性格呢,也属于可变型的,青年时懵懂,中年时暴躁,壮年时包容,老年时乖顺。我们父子之间,打我长大成人就有了隔膜,我不满父亲的棍棒教育,父亲嫌我烂泥扶不上墙。我们爷俩做事都是拧巴着来,他给我报名参军我偏不去,第二年我偷偷参军不跟他商量,父子关系降到冰点。一直到我被“父遭车祸,速回”的电报催回家,见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父亲才起恻隐之心。后来,我在部队提了干,又拉出两个弟弟出去当兵,为父亲分忧解难,父亲从来没当面夸过我,但他的一次表现,表示与我冰释前嫌了。小弟偷邻居家枣被人家找上门,父亲把自己的鞋脱下来扔给我:“老大,我老了,打不动了,你上!”说明他服我了,要把这个家交给我了。可之后父亲又对我进行考验,在没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突然杀到部队。家里明明有套新中山服,却穿一件旧棉袄,一条带补丁的劳动布裤子,堂而皇之地站在军营门口等我来接。意思是看看你这当军官的儿子,对土的掉渣的农民父亲到底是啥态度,搞得我哭笑不得。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弄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最难懂的是父亲,而最难忘的也是父亲。
在叙述方式上,我采用了父子对话,时空穿插的手法。一条线是父亲在农村的生活,一条线是我在部队的成长经历,两条线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父亲每做一件事,都与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部队每前进一步,都感到背后有父亲的一双手在推动,我人生中的每一次蜕变都镌刻着父亲言传身教的印记。另外,在风格上,我既遵循散文的创作原则和特点,又充分发挥小说创作的优势。大篇幅采用白描手法,始终保持克制冷静的态度,不过分渲染感情,尽量把一地鸡毛的事,说的津津有味,把四平八稳的事,讲的跌宕起伏,把撕心裂肺的事,叙述得气定神闲。再就是语言追求地域化、个性化、口语化,让农村文化与军营文化达到契合,让读者读起来轻松且有味道。
我更知道,我的倾诉应有其价值意义。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认为,长篇叙事散文也应承担这样的使命。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民军队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军营文化流淌着农民文化的血脉,百分之八九十的军人都有一个农民父亲。若干年以来,以军人视角描写农民父亲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少,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曾一度掀起“农家军歌”的创作热潮。我以《农民父亲》为代表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也属于这一谱系。时隔这么多年,如果我们再重复写这一主题,读者会有较高的阅读期待,这就逼着我要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在军人眼里,家是浓缩的国,国是放大版的家,有国才有家。父亲百年人生岁月中虽然没有正式参加革命的生涯,但在抗战时期,曾为回民支队抬过伤员,赶着马车为拔鬼子据点的八路军送过粮食,在“五一大扫荡”中和冀中抗日军民一起坚壁清野,天津解放,与工友们举着小旗一起上街游行欢庆胜利。到了中老年,他把三个儿子送到部队,使得他一直到六七十岁,还在家里当壮劳力使。他曾多次对我们说:“我没能耐给你们找出路,但只要你们出去为国家效力,家里再用人,我也不拦着。”三个儿子一道回家省亲,他说:“你们穿着军装,不能光图外表光荣,要像杨家将一样为国尽忠。”我呢,当了40多年兵,虽然没上过战场,但作为文艺战士,第一时间赴抗震救灾、抗洪抢险前线采风创作,父亲让弟弟把电话打到前线,为我鼓劲加油。我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撰写解说词,完成任务回到家,父亲为我举杯庆贺。我的立功喜报寄回家,向来低调的父亲一张一张小心翼翼地贴在墙上。
在我的军旅生涯中,在父与子、家与国、孝与忠发生冲突的时候,我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最后只能做出别无选择的选择。常言说,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最好的床前尽孝,就是义无反顾地为国尽忠,对父亲最大的回报,就是让自己的事业取得辉煌,从而实现“小家遗憾”到“万家守护”的升华。正如曹植《白马篇》中所云:“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在《父子书》的叙述中,我强化了家国情怀与忠孝观念的共同价值,强化了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融合。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家国同构,而家国同构的实质就是把个体命运融入国家命运。我在叙述父亲百年历史和我40余年军旅生涯的故事中,竭力把“小我”融入“大家”,把个人叙事融入宏大历史事件,继而摆脱感念化的表达,努力使父与子的形象获得血肉丰满的文学品质,这应该是我向着天堂倾诉的初衷。